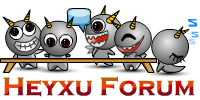???半夜的时候被叫起来导尿,在附件病房事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,但这次却是个女患者,
「女病患尿不都是由护士负责的吗?」我问。
「抱歉,赖医师,她的很难导,要麻烦你一下,」护士满脸歉意地说。
於是,我步入病房,床上躺著一位清秀的女病患,身旁则站著一个斯文的男士。
他一看到我就说∶「医师,对不起,三更半夜把你叫起来,可是她实在是胀得受不了了。」
拿起导尿管,我试了一下,管子硬是卡在膀胱颈进不了膀胱。
我想可能是膀胱颈痉孪,这在脊髓损伤病患中相当常见。
我立刻吩咐护士,打一针松弛剂试图使膀胱颈放松。
再试一次,果然通了进去,导尿管内才汩汩地流出近一千毫升的尿液。
「完了,这下膀胱准胀坏了,又得再费事做膀胱训练」我心想。
在处理过程中,我与他俩闲聊,终於知道整个故事的轮廓。
这对恋人,在同一所国中任教。一天,两人相约同游青翠的山谷,未料竟发生意外,
女老师失足坠落深谷,摔断脊背,造成半身瘫痪,开完刀虽已近三个月,大小便仍无法控制,而男老师也一直陪伴在病榻一旁。
隔天,教授查房,住院医师报告女老师病情摘要後,
教授缓缓摇摇头说∶「已经三个月了,一点进展也没有,复原机会不大。」
我在笔记上纪录下这段话。女老师的头偏向墙壁,在大夥儿将目标一向下一床病患时,我依稀听到她的哭声,男老师则在一旁轻握著她的手。
「 开我吧,我不会好的,」她说。
他坚定的摇一摇头说∶「都是我的错,我要照顾奶一辈子。」
「傻瓜,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,和你无关。」她忽然提高音量。相当激动,大家,包括教授,都转身望向他们。
「你已经请假快超过三个月了,再请,学校会要你辞职,」她激动地说。
男老师仍坚持地说∶「辞就辞嘛,我教了几年书,还有一点积蓄。」
女老师忽然歇斯底里地大喊∶「医师,他要骚扰我,快把他 走,快来人哪,他是个疯子,你们医院搞什麽,还不把他 走。」经过一阵喧闹,我们只好将男老师请出了医院。
女老师复原状况果然不出教授所料,一直无法突破。尤其在她 走男老师後,护士说她常暗自流泪。好几次,男老师捧著花束来,都被他高升叱喝而走。最後一次,她扬言如果他再来就要自杀,从此再也没见过男老师了。
某夜,又轮到我值班,正在为女老师邻床的病患换药,突然听到一位中年妇人向她致谢∶「多谢奶能体谅我们做父母的心,幸亏奶深明大意,不然我那个儿子,真会为奶一辈子不娶了。」
只听女老师幽幽地说∶「伯母,志雄是个好人,愿意嫁他的人一定不少,我不能再拖累他了。」
我这才恍然大悟,为什麽她一定要 男老师走。
我原以为是女老师接受不了半身瘫痪的事实──发疯了。
那天晚上,她流了整夜的泪水。
「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,怕哭升吵到邻床,总是掩住口鼻哭泣,」护士说。
时光飞逝,过了一个月,她的膀胱训练终於成功,可以自己控制大小便,臀部的褥疮也愈合了。接下来的是更艰难的步行训练。
她必须大费周章的绑好两枝重达两公斤的长腿支架,再撑起两根腋下的杖,才能挣扎站起来,勉强地拖行。
第一步尝试便摔了一跤,幸好旁边有治疗师扶住。
她咬著牙,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著。「我好想念班上的学生,」她说。
就这样,她竟也一步一步用杖走了起来,只是步伐还不稳,常常摔跤。
奇怪的是,自从她转到一楼运动治疗室训练步行後,倒是常瞥见有个带帽子及墨镜的男子站在远处。
「是其他患者的家属吧,」我想。
「赖医师,你知道吗?那个女老师常在半夜到长廊练习走路,」护士偷偷告诉我。
「或许,她真的可以走出医院哩,」我想。
但是耳边马上又回响出那一段话∶「超过三个月,不可能复原了。」
那天晚上,不是我值班,却始终无法入睡。
我索性回到病房,整理了一些病历,好为隔日查房做准备。
忽然我听到长廊那头响起一阵「呵,呵」声,伸头望去,只见女老师孤零零的背影拖映在冰冷的长廊上,她正在练习走路。
「糟了,今天早上长廊的那一头才刚上了新蜡,中午还有一位家属在那儿摔倒,何况是不良於行的她了。」我的警觉太慢了,只见她摇晃一下,身体就像被砍倒的树一般,扑向冷硬发亮的地板。
「完了,」我大叫一声。
突然,从旁边冲出一个黑影,即时拉住她的衣襟。
但重量可能太重了,或者地板太滑了,两人便一起摔跤在地板上。
多亏这即时的一拉,落地的声音显然比预期小多了。
「志雄,你这又何苦。。。。」长廊尽头传来这句话。
我急忙 过去,差点也摔了一跤。
只见散落一地的杖、帽子、墨镜和地板上那对苦命鸳鸯。
「你们不要紧吧,」我一边检查有无外伤,一边问她
「不要紧。」女老师挂著泪珠的面庞第一次出现笑容。
「医师,去跟教授说,我一定要走出去,」女老师握著男老师的手说。
之後,病房内又看到他们形影不 地做复健。
隔不久,我被总院调到外地支援,回来时,女老师已出院。
不知是哪一天,阳光悄悄洒满了长廊。
我相信自己一定是眼睛花了──她们竟向我走了过来。
女老师笑得像一朵花似的说∶「赖医师,我回来做检查的,一切正常。」
我楞在原地,许久说不出话来。「不用穿支架,不用杖,一切正常。。。。怎麽可能?怎麽可能??」
「赖医师,我们走棉。」男老师向我挥一挥手,女老师也向我说了一声「再见」。
「不,不要说再见,」我笑著大声回答,顺便撕掉那一页记著「超过三个月不可能恢复」的笔记。
祝福你们,我亲爱的朋友。
你们让我学了很多,但,不要说再见。
「女病患尿不都是由护士负责的吗?」我问。
「抱歉,赖医师,她的很难导,要麻烦你一下,」护士满脸歉意地说。
於是,我步入病房,床上躺著一位清秀的女病患,身旁则站著一个斯文的男士。
他一看到我就说∶「医师,对不起,三更半夜把你叫起来,可是她实在是胀得受不了了。」
拿起导尿管,我试了一下,管子硬是卡在膀胱颈进不了膀胱。
我想可能是膀胱颈痉孪,这在脊髓损伤病患中相当常见。
我立刻吩咐护士,打一针松弛剂试图使膀胱颈放松。
再试一次,果然通了进去,导尿管内才汩汩地流出近一千毫升的尿液。
「完了,这下膀胱准胀坏了,又得再费事做膀胱训练」我心想。
在处理过程中,我与他俩闲聊,终於知道整个故事的轮廓。
这对恋人,在同一所国中任教。一天,两人相约同游青翠的山谷,未料竟发生意外,
女老师失足坠落深谷,摔断脊背,造成半身瘫痪,开完刀虽已近三个月,大小便仍无法控制,而男老师也一直陪伴在病榻一旁。
隔天,教授查房,住院医师报告女老师病情摘要後,
教授缓缓摇摇头说∶「已经三个月了,一点进展也没有,复原机会不大。」
我在笔记上纪录下这段话。女老师的头偏向墙壁,在大夥儿将目标一向下一床病患时,我依稀听到她的哭声,男老师则在一旁轻握著她的手。
「 开我吧,我不会好的,」她说。
他坚定的摇一摇头说∶「都是我的错,我要照顾奶一辈子。」
「傻瓜,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,和你无关。」她忽然提高音量。相当激动,大家,包括教授,都转身望向他们。
「你已经请假快超过三个月了,再请,学校会要你辞职,」她激动地说。
男老师仍坚持地说∶「辞就辞嘛,我教了几年书,还有一点积蓄。」
女老师忽然歇斯底里地大喊∶「医师,他要骚扰我,快把他 走,快来人哪,他是个疯子,你们医院搞什麽,还不把他 走。」经过一阵喧闹,我们只好将男老师请出了医院。
女老师复原状况果然不出教授所料,一直无法突破。尤其在她 走男老师後,护士说她常暗自流泪。好几次,男老师捧著花束来,都被他高升叱喝而走。最後一次,她扬言如果他再来就要自杀,从此再也没见过男老师了。
某夜,又轮到我值班,正在为女老师邻床的病患换药,突然听到一位中年妇人向她致谢∶「多谢奶能体谅我们做父母的心,幸亏奶深明大意,不然我那个儿子,真会为奶一辈子不娶了。」
只听女老师幽幽地说∶「伯母,志雄是个好人,愿意嫁他的人一定不少,我不能再拖累他了。」
我这才恍然大悟,为什麽她一定要 男老师走。
我原以为是女老师接受不了半身瘫痪的事实──发疯了。
那天晚上,她流了整夜的泪水。
「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,怕哭升吵到邻床,总是掩住口鼻哭泣,」护士说。
时光飞逝,过了一个月,她的膀胱训练终於成功,可以自己控制大小便,臀部的褥疮也愈合了。接下来的是更艰难的步行训练。
她必须大费周章的绑好两枝重达两公斤的长腿支架,再撑起两根腋下的杖,才能挣扎站起来,勉强地拖行。
第一步尝试便摔了一跤,幸好旁边有治疗师扶住。
她咬著牙,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著。「我好想念班上的学生,」她说。
就这样,她竟也一步一步用杖走了起来,只是步伐还不稳,常常摔跤。
奇怪的是,自从她转到一楼运动治疗室训练步行後,倒是常瞥见有个带帽子及墨镜的男子站在远处。
「是其他患者的家属吧,」我想。
「赖医师,你知道吗?那个女老师常在半夜到长廊练习走路,」护士偷偷告诉我。
「或许,她真的可以走出医院哩,」我想。
但是耳边马上又回响出那一段话∶「超过三个月,不可能复原了。」
那天晚上,不是我值班,却始终无法入睡。
我索性回到病房,整理了一些病历,好为隔日查房做准备。
忽然我听到长廊那头响起一阵「呵,呵」声,伸头望去,只见女老师孤零零的背影拖映在冰冷的长廊上,她正在练习走路。
「糟了,今天早上长廊的那一头才刚上了新蜡,中午还有一位家属在那儿摔倒,何况是不良於行的她了。」我的警觉太慢了,只见她摇晃一下,身体就像被砍倒的树一般,扑向冷硬发亮的地板。
「完了,」我大叫一声。
突然,从旁边冲出一个黑影,即时拉住她的衣襟。
但重量可能太重了,或者地板太滑了,两人便一起摔跤在地板上。
多亏这即时的一拉,落地的声音显然比预期小多了。
「志雄,你这又何苦。。。。」长廊尽头传来这句话。
我急忙 过去,差点也摔了一跤。
只见散落一地的杖、帽子、墨镜和地板上那对苦命鸳鸯。
「你们不要紧吧,」我一边检查有无外伤,一边问她
「不要紧。」女老师挂著泪珠的面庞第一次出现笑容。
「医师,去跟教授说,我一定要走出去,」女老师握著男老师的手说。
之後,病房内又看到他们形影不 地做复健。
隔不久,我被总院调到外地支援,回来时,女老师已出院。
不知是哪一天,阳光悄悄洒满了长廊。
我相信自己一定是眼睛花了──她们竟向我走了过来。
女老师笑得像一朵花似的说∶「赖医师,我回来做检查的,一切正常。」
我楞在原地,许久说不出话来。「不用穿支架,不用杖,一切正常。。。。怎麽可能?怎麽可能??」
「赖医师,我们走棉。」男老师向我挥一挥手,女老师也向我说了一声「再见」。
「不,不要说再见,」我笑著大声回答,顺便撕掉那一页记著「超过三个月不可能恢复」的笔记。
祝福你们,我亲爱的朋友。
你们让我学了很多,但,不要说再见。
- 关键字 : 高升叱喝而走, 附件病房事一件稀松平常, 阳光悄悄洒满, 长廊尽头传来这句话, 这才恍然大悟, 这下膀胱准胀坏, 转到一楼运动治疗室训练步行後, 超过三个月不, 超过三个月, 赶走男老师後, 许久说不出话来, 要照顾奶一辈子, 膀胱颈进不, 膀胱颈痉孪, 膀胱训练终於成功, 脊髓损伤病患中相当常见, 者地板太滑, 绑好两枝重达两公斤, 经过一阵喧闹, 索性回到病房
00
2008-12-13T16:43:43+0000